多伦多的夜,被枫叶体育馆一万九千个喉咙里迸发的声浪炙烤得发烫,记分牌上,猛龙与凯尔特人的比分像两头抵死角力的猛兽,齿缝间渗出猩红的“98:98”,时间,只剩最后的7.2秒,波士顿的绿色浪潮在客场一角沉默地汹涌,塔图姆抿着嘴唇,眼神如北岸花园球馆外冬日查尔斯河的冰。
七秒,在篮球世界足以诞生神话,也足以埋葬英雄,猛龙的边线球,像一叶在惊涛中颠簸的扁舟,险些被斯玛特盗走,混乱中,皮球跌跌撞撞,竟滚向左侧底角——一个战术板从未预设的位置,一个灯光似乎都略显黯淡的角落。
那里站着布兰登·英格拉姆。
他刚刚在底线与杰伦·布朗进行了一场整整42分钟、寸土不让的肌肉绞杀,他的球衣湿透,紧贴清瘦的躯干,额前鬈发被汗水浸成深色,这个夜晚,他的数据栏并不华丽:17分,6篮板,4助攻,淹没在西亚卡姆的冲击与范弗利特的神经刀之下,凯尔特人用层层叠叠的防守告诉他,通往篮下的每一条路都是荆棘王座。
时间还剩3秒。
英格拉姆俯身,拾起那个不听话的皮球,动作轻得像拾起一片羽毛,杰伦·布朗的阴影瞬间笼罩,长臂遮天,那是本届最佳防守阵容级别的压迫,没有空间,没有助跑,甚至没有一次像样的晃动,英格拉姆所做的,只是微微向后漂移,在身体与地面构成那个最违背力学常识的夹角时,拔起,出手。
他的身形在空中舒展,像一把缓缓拉满的、寂静的弓,场馆的喧嚣在那一刻被抽成真空,只剩篮球脱离指尖的微不可闻的摩擦声,皮球划出的弧线极高,仿佛要穿越体育馆的穹顶,去触碰加拿大清冷的夜空。

网花泛起时,声音是清脆的“唰”,紧接着,是足以震碎耳膜的轰然巨响,以及红灯刺眼地亮起——100:98。
英格拉姆没有咆哮,没有捶胸,他只是缓缓落下,在波士顿人凝固的绝望与多伦多爆发的狂喜之间,转过身,用食指静静抵住自己的嘴唇。
走回替补席。
这个动作,比任何怒吼都更具统治力,仿佛刚才那记射落星辰的子弹,于他而言,不过是呼吸般自然的事情,队友们疯狂地扑上来,他只是微微颔首,嘴角有一丝几乎无法察觉的弧度,这就是“大场面先生”的注解:激情内燃为冰,压力淬炼成刃,在最灼热的熔炉中心,他反而呈现出一种极致的“冷”。
赛后,更衣室人声鼎沸,记者将长枪短炮对准他:“布兰登,最后一投你在想什么?”
英格拉姆用毛巾擦着头发,语气平静无波,仿佛在描述别人的壮举:“没什么,球来了,时间到了,就投了,那是我的位置。”
“我的位置”,轻描淡写的四个字,背后是数千个小时独自面对空旷球馆的打磨,是无数次在脑海预演绝杀时刻的冥想,大场面从不创造英雄,它只是为英雄准备好舞台,而英格拉姆,永远是那个当帷幕拉开、灯光聚焦时,早已在台上静候多时的舞者。

这一夜,北境猛龙用铁血撕咬,捍卫了主场,而布兰登·英格拉姆,用一记烙印在时间尽头的投篮,向世界宣告:有些人的心脏,生来就为最后几秒的绝对寂静而跳动,惊雷,总爱在无声处炸响。
版权声明
本文仅代表PGSoft观点。
本文系作者授权PGSoft发表,未经许可,不得转载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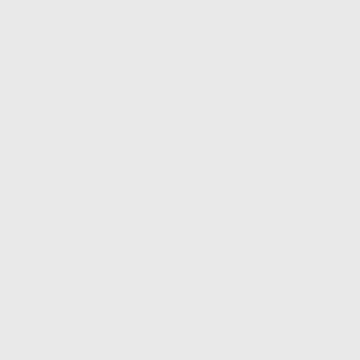
评论列表
发表评论